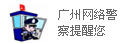涉外勞動爭議訴訟適用勞動合同法還是勞動局管理規定
人民大學法學院關懷教授認為,對于涉外勞動關系中的爭議糾紛如何適用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的問題,一直在我國勞動立法中處于空白。隨著涉外勞動關系越來越深入地滲透到我們的經濟生活當中,以及勞動法律的不斷完善,立法部門需要對這一特殊類型的勞動關系、特殊勞動群體進行明確規范。
最近,在上海工作的加拿大人KEITHCHANG(中文名字陳德基)先生非常苦惱。因為他與飛世爾試驗器材制造(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飛世爾公司)的勞動合同糾紛,上海市南匯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他敗訴。陳先生對記者說,因為不論是依據《勞動法》,還是《勞動合同法》,他的情況都不符合用人單位可以單方解除勞動合同關系的法定條件。但是讓他難堪的是,上海市勞動局1998年發布的《關于外國人在中國就業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明確規定,用人單位與外國人之間的勞動合同解除遵循雙方的合同約定。而上海法院在審理相關案件時一般也都采用意思自治原則來審判案件。
“一方要終止合同只須提前一月書面通知”
2006年年初,飄洋過海的陳德基來到飛世爾公司擔任副總經理。同年的5月,陳先生和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根據約定,雙方的勞動關系始自2006年1月1日,合同期限為一年。合同期滿后,除非有一方在開始延長合同之日前至少兩個月提出書面的不續簽合同意見,否則聘用合同自動延長,每次延長3年;合同任何一方要終止合同必須提前一個月提出書面報告。
很快,一年的合同期限滿了。由于陳德基和公司在約定的期限內都沒有提出不續簽合同的意見,按照聘用合同的約定,陳德基與飛世爾公司的合同期限自動延長到2009年年底。不料,情況突然出現逆轉。2007年5月,飛世爾公司向陳德基提出解除勞動合同,并提供了《勞動合同解除協議》和《保密及非競爭協議》。對此,陳德基通過發律師函的形式表示不能接受。5月30日,飛世爾公司又向陳德基發出終止勞動合同通知書。于是,陳德基向上海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要求飛世爾公司繼續履行當初的勞動合同。
然而,上海市勞動仲裁委只裁決飛世爾公司支付一個月提前通知期的工資,對于陳德基繼續履行合同的請求不予支持。這樣陳德基又委托律師向上海市南匯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法院經審理認為,陳德基與飛世爾公司的聘用合同明確了雙方的權利、義務,陳德基是在上海市就業的外國人,根據“上海市勞動局關于貫徹《外國人在中國就業管理規定》的若干意見”(簡稱“若干意見”)第十六條規定,用人單位與獲準聘雇的外國人之間有關解除聘雇關系涉及的雙方權利義務,由勞動合同約定。飛世爾公司與陳德基在聘用合同中明確約定任何一方要終止合同必須提前一個月書面報告,而飛世爾公司又是按照這一約定解除雙方勞動關系,行為并無不當。因此一審判決沒有支持陳德基的請求。
據陳德基的代理律師朱亮介紹,對于涉外勞務糾紛中有關合同解除、終止的問題,上海法院一般都參照的是“若干意見”規定,即雙方的勞動合同約定,采用意思自治原則來判斷勞資雙方的責任。也就是說,既然陳德基與公司當初約定“任何一方要終止合同必須提前一個月書面報告”,那就按照該約定。但是這種約定明顯不符合勞動法或勞動合同法有關單方解除合同的規定,而且飛世爾公司也提供不出任何證據證明陳德基有法律規定的合同解除情形。如果一審判決成立的話,用人單位豈不是隨意可以炒員工“魷魚”!因此,陳德基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是否意思自治看法不一
朱亮律師認為,法律對于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條件規定得很明確,而在中國境內為中國企業服務的外國員工,應該也屬于勞動法律調整規范的對象。飛世爾公司不能通過合同約定的方式,以“只要提前一個月書面通知”為單方解除合同的條件,來規避法律對此的限制性規定。勞動法是不允許以雙方事先約定的情形作為解除條件的,否則勞動法限制性規定將沒有任何意義。
出臺于1998年的“上海市勞動局關于貫徹《外國人在中國就業管理規定》的若干意見”第十六條就規定,用人單位與獲準聘雇的外國人之間有關聘雇期限、崗位、報酬、保險、工作時間、解除聘雇關系條件、違約責任等雙方的權利義務,通過勞動合同約定。
這個地方部門規章,成為上海當地法院裁判解決這類糾紛的主要法律依據。其中原因何在?曾就職于上海市某基層法院的某法官向記者解釋說,有關勞動合同單方解除的條件是可以通過合同約定的方式進行明確的。因為這屬于勞動合同意思自治原則的范疇。而勞動法或者是勞動合同法所規定的上述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合同限制規定,不是排他性法律規定。勞動法并沒有禁止合同約定用人單位的解聘條件。也就是說,在沒有約定的情況下,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必須符合上述幾個條件。但如果有約定,則遵從合同約定。
對于意思自治處理原則,北京市一中院民一庭某法官認為,意思自治原則也應該有一個范圍,勞動合同的約定不能違反法律規定。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屬于公法范疇,主要體現保護勞動者利益的精神。法院在處理這一類型案例時,一般要看雙方的聘用合同與先行法律有無沖突,違反法律則認定為無效。
北京市高院民事審判庭某法官提出,對于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條件,勞資雙方是可以進行約定的,但這個條件不能低于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保護的標準。因為用人單位行使單方解除勞動合同權利,這牽扯到勞動者的就業權利。如果允許用合同約定的方式降低或規避法律給予勞動者的權利保護,那么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有關限制用人單位單方解除權的規定將變得毫無意義。而勞動合同法對于用人單位單方解除權的限制性規定,是勞動者在這個方面受保護的最低標準。勞資雙方的合同約定保護水平不能低于該標準。
涉外勞動關系意思自治范圍需規范
在我國,保證勞動合同關系穩定和保護勞動者利益是《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重要精神。對于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勞動法做了嚴格的規定。
有業內人士分析,京滬兩地法院對于因合同約定用人單位單方解除權引發糾紛的不同處理方式,反映了這兩個地區司法部門在涉外勞動合同關系中,對于意思自治原則理解的不同。換句話就是,怎么理解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關于用人單位單方解除權的限制規定?這是否就是強制、排他性的法律規定?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勞動法專家金英杰教授認為,對于涉外勞動合同關系,既遵循合同意思自治原則,也要遵循勞動關系最密切聯系國家法律的原則。
在我國,對于用人單位的解聘權是受到限制的,實施對勞動者解聘保護的政策。這包括用人單位單方解聘必須符合法定條件、有一定的解聘程序規定、需支付經濟賠償金以及法定的禁止解聘情形等限制規定。而這些規定帶有強制性色彩,勞資雙方不能通過合同約定的方式來規避。外國人與我國境內的用人單位締結勞動關系的合同,當然受我國勞動合同法的規范,因此即使是涉外勞動合同關系,對于用人單位的解聘權利進行約定也不能違反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規定。
勞動法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關懷教授認為,對于涉外勞動關系中的爭議糾紛如何適用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的問題,一直在我國勞動立法中處于空白。當初由于我國勞動法律體系還不夠完善,對于這種涉外勞動合同關系,一般采取由勞資雙方合同約定的方式來處理。但是隨著涉外勞動關系越來越深入地滲透到我們的經濟生活當中,以及勞動法律的不斷完善,立法部門需要對這一特殊類型的勞動關系、這一特殊勞動群體進行明確規范。
關懷教授說,其實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只要是與中國的用人單位產生勞動聘雇關系,就都是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者,都應該遵守我國勞動法律規定。目前正是因為這些法律空白,才導致各地方在處理同一類涉外勞動關系糾紛問題時所采取措施的不同。他建議,應該在接下來制定的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當中,對涉外勞動合同關系進行專門規定,對于其中所涉及的一些普遍問題予以明確,以此保證勞動合同法的順利實施。
上一篇:如何確定勞動爭議發生之日
下一篇:勞動爭議糾紛訴訟三技巧
熱點文章點擊
- 01工傷賠償標準2015
- 02工傷認定的情況、申請時間
- 03病假的天數是怎么計算的
- 04最新勞動仲裁申請書
- 05辭職的流程
- 062015年生育生活津貼標準如何確定